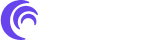“氽”和“汆”
“氽(tǔn)”和“汆(cuān)”,这两个上海方言字,眼力不好的话,常容易搞混。
“人在水上”为“氽(tǔn)”,“人在水下”为“氼(nì)”。“氼”是“溺”的古体字,是我国秦汉前古人版的“溺”字。两者是互通关系,但前者词意范围要小于后者(按:“氼”侧重于原始沉没之意,没有“尿”的含义。后汉字在演变过程中,“溺”字逐渐被官方文书采用,成了日常交流中的主流用字)。
真佩服我国古人造字的博大精深,将两个(或两个以上)已有的独体字,巧妙地组合起来,来表示一个新的含义,此种造字方法就是汉字六书之一,称之为“会意”(大多组成为一个新的动词)。望“氼”生义,“会意”一下:“人”落下“水”,掉入江中,水淹人头,挣扎几下,“氼”(溺)水而亡,人就成了“落水鬼”了。可在水中也溺毙不了几天,尸体会因自身内部腐烂充气(即“吃饱水”巨人化了)而浮上水面,上海人把这种“人在水上”状况称之为“氽”。
氽(tǔn),上“人”下“水”,沪音与“吞”音相近,本义表示“人或物体漂浮于水面”。
“长江第一漂”尧茂书,其实就是借助长江源头的水势,乘坐自制的皮筏,由上而下、随波逐流顺势“氽”下来时,不幸的是他中途没掌控好,触礁遇难,葬身江中。真是水能“氽”筏也能覆筏,对此只能是深感惋惜!
——以上这种只是一种随势漂流的动态的“氽”,还有一种浮在水面、不太动的静态的“氽”。过去(浦西)南码头附近有家(久记?还是南市?不记得了)木材厂,成排的圆木桴栰终日“氽”在黄浦江畔;因刚砍下树木是不能直接用的,需在水中“氽”泡一段时间。成年累月后的圆木(失去应力不会变形后),才能进厂锯成板材,发挥作用。
上海七宝古镇,有口明永乐合金(金、银、铜、铁、锡五金)熔炼而成的“钟”,高近二米,直径一米,壁厚近十厘米,因其重达一吨,只能通过水路从蒲汇塘运至七宝寺,故名为“氽来钟”。“氽来”,即老天爷借用“水势之力,漂浮而来”之意,是传说中属于古镇保存至今的唯一实物,也是“七宝”的文物之一(金字莲花经现藏于上海历史博物馆,其他“宝物”已不见踪影了)。
黄浦江、苏州河等水域,过去最常见的环境问题,除了氽在江河水面上的垃圾外,就是杂夹在垃圾中的“浮尸”,即大多从上游漂浮而下的乳猪尸体。旧时农村不像现在讲卫生,小猪死了就随手往小河内一丢。随着潮汐的涨跌漂荡,氽法氽法,在潮汐的作用下,死猪就从乡下飘河过江,“氽”到大上海来到此一游了。
当然黄浦江没有盖头,不免有些想不开、寻死觅活要跳黄浦的,或有极个别的沉尸刑事案,没过几天沉尸也会浮上水面,上海有句地道方言词来形容,叫做“氽江*浮尸”(*按:其中“江”,方言音为:gāng钢)。
日常生活中,我们烧馄饨水饺、或煮汤圆肉丸时,下水后等它们氽上来了(即“浮起来”)就表示熟了。
“氽”,原指物体漂浮水面上的一种自然现象,后被沪语引申到了食物加工中的烹饪术语,类似于“油炸”。
上海人最熟悉的,莫过于承载了几代人味觉记忆的、传统早餐中的油氽油条、油氽粢饭糕,以及过去各家饮食店午后门口摆摊常见的油氽麻油馓子、油氽油墩子、油氽“开口笑”、油氽月牙糕(糯米豆沙馅,形状类似于一只大型水饺)、油氽麻球、油氽糖糕、油氽年糕(一种像“鲜得来”薄型的,不是现在外面市场买的那种年糕)等传统街头小吃点心。刚从油锅里氽出来的食物,香气四溢;现氽现吃,覅太“赞”噢。而在家中最简便易操作的下酒菜,莫过于油氽一碟花生米、豆瓣或腰果之类东西了。至于《西游记》中的孙悟空,是否在油锅中被油氽翻滚过,因是早年看的,现早已是忘了该书情节了。
与“氽”最易搞错的,就是“汆”了。
“汆(cuān)”,上“入”下“水”,沪音与“窜”相近,表示将食材“投入”沸水中,稍微一煮随即取出,以防食物养分流失,或防食物变老、变黄,保持食材本身的鲜嫩。词义类似于普通话中的“焯(chāo)”一下, 也是一种烹饪方法;但“汆”更强调短时沸水处理,如:汆丸子、汆烫(刷)牛羊肉、汆烫鱼片、鲫鱼汆豆腐汤等……;而“焯”涵盖冷、热水预处理食材,如肉类“焯”水去血污杂质、腥膻异味等。
有些蔬菜草酸含量较高,需水中“汆”一下,去掉一些草酸或异味。如:菠菜、苋菜、荠菜、马兰头、香椿、苦瓜、茭白、竹笋(鲜竹笋)等……,需注意的是:绿叶类蔬菜(如:菠菜、苋菜),“汆”水时间可短些;根茎类蔬菜(竹笋、茭白、萝卜等)可稍需长些,确保其草酸被充分分解掉。“汆”水后需立即用冷水冲洗过凉,以确保持其蔬菜色泽鲜艳和口感爽脆。
“汆”字还有个义项,即引申为把东西丢入水里或人钻入水中。如“剑忽于腰间跃入水,使人汆水求之(见张岱《夜航船·兵刑部·军旅》)”。
总之,“氽”和“汆”两字,形虽相似,而音义相远,需仔细辨别。两者皆是烹饪术语之一,都可作为动词,可它们食物加工的手法也不一样。
“人水”为“氽”,“入水”为“汆”,“人”与“入”可要辨清噢?
二〇二五年四月九日午后
(注:您的设备不支持flash)